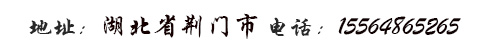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想到自己的童年
|
北京医院湿疹治疗 https://m-mip.39.net/czk/mipso_8814675.html 最近在重读《朝花夕拾》,发现鲁迅虽然生长在没落的地主家庭,但他小时候可比我小时候好玩多了。 我们都从《呐喊自序》中读到过鲁迅生活的突变,“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他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这些对突变之后的生话的记叙,能够给我们艰辛无奈又压抑的既视感。我们或许便因此以为鲁迅的童年非常不幸,其实不幸是后来的事,在此之前,他还是很快乐很充实的。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到的园子。 如今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样的园子,即使有也未必这样的好玩。来温习文章的第二段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这段文字自从进入教材以后,成了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文字中间或许有鲁迅回忆童年时的一种美化,因为只要去过绍兴鲁迅故里,看过百草园,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块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地方。但芟去语言辞藻铺排所美化的成分,再根据文章用想象补上那些消逝了的动植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百草园的的确确是一个儿童的乐园。不必说后文所写的美女蛇的恐怖、雪中捕鸟的乐趣、三味书屋的好玩,仅第二段所写的这富有生机的几十种小生灵的名目,都能让人羡慕死。 我家门前有一个一两个平方大小的天井,后门外也有一个三四个平方大小的园子,但全没有鲁迅所写的百草园那么好玩。天井由于过于狭小,没法玩,所以没有什么存在感。只有在下雨天,雨水丝丝落下,天井中微漾着水花,我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有一回,我往天井中放生了一只小乌龟,然后——当然就再也没有看到它的踪影。这算是我在天井中自主养殖的失败。这只小乌龟要是活到现在,也该有40多岁了吧。后门外也有一个园子,但比起西邻的园子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西邻家可以种甘蔗种橘子,广大而有些荒芜,适宜发生《聊斋》一样的故事。而我家的由于实在太小,只是搭了一个屋棚,往里面存放一些农具杂物,并无真正的园子该有的样子,自然也不是我玩的地方。 另一个例子是《五猖会》《无常》中所写到的迎神赛会。 鲁迅小时候看这些带有浓厚迷信色彩却又令人惊异的活动,就如同现在的小孩子看神话题材的动画片。而我小时候,这些东西虽然还在,却只剩一些余光,而绝没有那样盛大了。 比如元宵节的盛大游行活动,我朦胧记得曾在四五岁的时候,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看到过一次。现场锣鼓喧天,气氛热烈,万人空巷。但就算我坐得高,也只看得到有人踩着高跷,其他一概没看到。这是唯一的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过。元宵游行活动是城里举行的,而农村则有自己的七月七晚上的“五猖会”。半夜时分,有一群人,抬着无常、判官、神鬼的塑像,浩浩荡荡又静静悄悄地在各村行走。老人们都会迎出去焚香祝祷,然后就在水边放河灯。河灯不是如诗如画的那种莲叶灯、鱼儿灯,只是用稻草挽一个结,上竖白烛,让它随水飘走。简化暗示了习俗由繁入简的变化。这种暗夜游行我也只在十多岁的时候听到看到过一两次,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比起鲁迅那时候所见所闻所玩,我小时候的景况都要简陋寒酸一些,使我不免有些遗憾。但比起现在的孩子们,我又何尝不是幸运的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ouwutenga.com/swthj/11107.html
- 上一篇文章: 白芍何首乌天冬的药用部位,及种植技术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