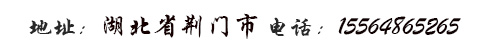没有儿童节的时代,大师们的小时候是如何过
|
你好!我们是“悦读悦享” 绘本和儿童阅读的疯狂热爱者和沉静思考者 劳动节没有劳动,情人节没有情人,圣诞节没有圣诞老人,至少,儿童节还能做一天的孩子吧。 胡适《我的母亲》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国,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尽于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莱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呜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岭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役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宇,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商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西撒些秋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士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担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我的蟋蟀们!Ad,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老舍《老舍自述》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 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林语堂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安排诵诗童年,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时光还是活现脑中,依稀如旧的。记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宝鼎)至漳州。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毡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如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时,我愿以摄影快镜拍照永留记忆中,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一幅天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将来在年长之时回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尚有一个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厦门寻源书院最后的一夕。是日早晨举行毕业典礼,其时美国领事安立德(JulanArnold)到院演说。那是我在该书院最后的一天了。我在卧室窗门上坐着,凭眺运动场。翌晨,学校休业,而我们均须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静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该书院四年生活之完结日;我坐在那里静心冥想足有半点钟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脑中以为将来的记忆。我不能详述我的童年生活,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因为我们在弟兄中也不准吵嘴。后来,我要尽力脱去那一副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以去其痴形傻气。我们家里有一眼井,屋后有一个菜园,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儿女们于此,各人派定古诗诵读,父亲自为教师。不像富家的孩子,我们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劳作。我的两位姊姊都要做饭和洗衣,弟兄们则要扫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当姊姊们由屋后空地拿进来洗净晾干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时,我们便出去从井中汲水,倾在一小沟而流到菜园小地中,借以灌溉菜蔬。否则我们孩子们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远望日落奇景,而互讲神鬼故事。那里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环绕,故其地名为“东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巅上当中裂开,传说有一仙人曾踏过此山,而其大趾却误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 茅盾从小“文学迷”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 但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着名文学家。 林徽因早熟骗走了她的童年林徽因是父亲林长民和母亲何雪媛结婚八年后的第一个孩子。年6月10日,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祖父寓所。她是祖父长子的头生孩子,又是个女孩。祖父听说孙女出生的消息非常高兴,喜悦地吟诵出:“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因此为她起名为徽音。老人的意思,大概是要林徽因继承美德,再引出孙儿满堂吧。徽音改名为徽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她那时候经常发表作品,与另一个男性作者重名,所以改名为徽因。 林长民和许多同时代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在徽因2岁那年,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当时徽因很小,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却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在徽因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长年不在家的人,父亲的含义就是一封封从日本邮寄回来的信札。信都是写给祖父母的,自己和母亲就是那最后的一句问候。 上天给了林徽因一个十分优秀的父亲,为她安排的母亲却是一名极平凡的女性。林徽因的生母叫何雪媛,她的头脑像她那双裹得紧紧的小脚一样,守旧,甚至有点畸形。她出身于嘉兴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嫁给林长民做了妾。林长民才华超群,风流儒雅,善诗文,工书法,可她却是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她不懂琴棋书画,也不能操持家务,所以也就得不到公婆和丈夫的欢心。孩子的接连夭折,让公爹难免有断后之忧,由此引起的不满当然不言而喻。或许是林长民长年在外的缘故,林家看来相当克制,许久没有考虑再添妾。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的林徽因,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幼年的林徽因和一群表姐妹住在祖父的大院里,她喜欢和表姐妹们在一起读书玩耍。她的启蒙教育落在同住一起的大姑母身上,大姑母出嫁后依然常年住在娘家。几个女孩在一起,有的时候好得像一个人,有的时候又闹得不可开交,大姑母总是任由她们打闹。林徽因异母弟林暄曾回忆:“林徽因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大姑母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 5岁的林徽因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林徽因是旧式家族庶出的大小姐,来自族人的倾轧与磨难成为她的必修课。在失宠的母亲之外,她需另寻可倚重的亲情依靠。这位姑母弥补了林徽因母亲性格、文化方面的不足。林徽因很有灵气,大姑母经常夸奖她聪明灵秀,一起读书的几个姐妹中,徽因年龄最小,最贪玩,上课时候也不注意听讲,可是她却总是背书背得最好的。此时林徽因的天地有如祖父的庭院一般阳光灿烂。 徽因6岁的时候,出了水痘,按照老家的说法,这叫出“水珠”。她期盼着有人能来后院,不是她感觉到孤独,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她自己出“水珠”。她竟然不像许多孩子那样感到难忍的病痛,也不觉得这是病,她喜欢水珠这个名字,所以因为这个病多了几分骄傲和神秘。后来徽因回忆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这异乎寻常的感受已显露出她天性中的艺术气质。 父亲时常在外,只得留林徽因在祖父身边。她是个聪颖的女孩子,因此深得祖父、父亲的喜爱。她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平时,祖父经常给她讲这样那样的故事。她6岁开始为祖父代笔,给父亲写家信,成为祖父与父亲之间的通信员。 徐志摩头大到尾的顽皮孩子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而尤其是那个头大尾巴小(当时志摩长得头大身体小),戴金丝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文起来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这是作家郁达夫在志摩去世后的悼念文章《志摩的回忆》中,对中学时代徐志摩的一段回忆文字。当时,郁达夫与徐志摩是同级同班,而且住在同一宿舍。同住的还有志摩的表兄沈淑薇。 那时,十四岁的郁达夫刚刚从富阳转入杭州府中,一个久居乡下的少年突然来到省府城市,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可怕的,在课堂上、宿舍里自然也都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也不敢伸一伸”。 但和少年郁达夫的畏缩、羞怯相反,当时的徐志摩却尤其活泼好动,伶俐顽皮。在课堂上或宿舍里,他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中学时代志摩的活泼好动在性情内敛的乡下少年郁达夫的眼里,或许有因性格反差而致的夸张成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郁达夫的文字里看出志摩年少时的热情活跃、喜好引人注目、努力成为人群中心的脾性,其中包含着优等生所常有的那种自我优越感。 曹禺《童年锁忆》我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石,这是按着我父亲的字排下来的。我父亲叫万德尊,字宗石。还是在湖北省潜江县的时候,万家是个大家族,人口很多,但数我们这一房最穷了。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家境贫寒。父亲考进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每月有四两银子的津贴,他还得把一半银子寄回家中,接济家用。清朝末年,政府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去,我父亲选了这条路。那时,一般人是不愿意出洋的,只有那些经商的才敢去冒这个风险,就像《镜花缘》里的林之洋那样。我父亲决心去日本,去闯一闯,显然是把它看成是一条能光宗耀祖的道路。他被分配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他和军阀阎锡山是同学,即使在日本,也是相当早的毕业生了。我父亲毕业回国后,曾经当过师长,做了一个小军阀,但是,他为人胆子很小,又从来没有打过仗,加上他读书较多,便更像是个文人,四十多岁,他就不做事了,经常找几个诗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写点诗文。 我的家庭人口不多。我父亲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我的姐姐和哥哥是第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的母亲生我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得的是产褥热,那是不治之症。我的第三个母亲和我的生母是双生的姐妹。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是自命清高的,“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四十多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时才睡觉,傍晚才起床。每当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地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但是,这倒有一个好处,使我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我的住房很宽敞,家里房间很多,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还有一座小楼,也有许多房间,阔气得很,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说起来也令人奇怪,我父亲却常常对我说:你是“窭人之子”啊!“窭人”,是文言,也是湖北家乡话,就是说,你是个“穷人的儿子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父亲总是教训我要如何自立、如何自强,他让我千万不要去做官,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因此,他总是劝我去做医生。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我的英文学得不好,生物也学得不好,考了两次协和医学院都没有考上。可见,人生的道路,有时并不是靠主观意志所能安排的。我想,我父亲的那些话,对我萌发出一种贫富之间是不平等的观念,或许多少有些关系吧! 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亲非逼着我做诗。我哪里会写诗呢?想了许久,蹩出两句诗来:“大雪纷纷下,穷人无所归。”这叫什么诗呢?可是父亲却夸奖说:“不错,很有些见解。”现在回想,家里住着暖暖的房子,吃着火锅,能这样写,实在“难得”!其实,这也不离奇,公子哥儿从没有尝过穷人受苦的滋味,也能说这样的话。当然,寻根溯源,找个道理也行,从什么地方我得到这样一种感受呢?那时,我家里有个保姆,叫段妈,陪着我睡觉。有时,睡不着,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告诉我她丈夫是怎么死去的,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这些悲惨的事情。她的孩子死得很惨,身上长疮,疮上都是蛆,硬是疼死了。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好的保姆,真像一个人一生的启蒙老师;鲁迅的童年,长妈妈就给了他许多教益。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钱钟书“小吃货”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张爱玲“个性少女”张爱玲出生於旧中国曾经地位显赫的官宦家庭里。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着名清流派的代表,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父亲一身遗少作风,染有弄花捧月之恶习,因而夫妻不和。她的母亲是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曾经留过洋。张爱玲生长的这种家庭,既给了她得天独厚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修养,又使她形成敏感而又冷漠、孤僻而又实际的性格。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作家天赋。三四岁时,母亲就教她吟诵诗词。聪颖的她,一首诗词念不了几遍就会背诵。她读古典诗词有很好的悟性,读一首小诗往往能心有灵犀仿作一首。7岁左右张爱玲就能写小说了,看她那信手“涂鸦”之作,往往叫父母亲乐得手舞足蹈。小爱玲9岁那年的一天,她信笔画了一幅漫画,母亲说好,父亲也说好。她把漫画投给了报社,几天以后,从报社寄来了5元钱稿费,她高兴得跳起来。爸爸妈妈说:“这些钱就随你支配吧。”小爱玲兴冲冲地跑到商场,她买来了一枝丹琪唇膏,真叫父母亲哭笑不得。张爱玲上中学时,文才已充分显露出来了。她所在的学校是上海玛利亚女校,当时的学校有一种文学校刊叫《国光》,张爱玲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书评和论文。其中有一篇《霸王别姬》写得悲壮豪迈、慷慨激昂,直令许多男儿叹赏,其文辞灿烂,也令许多文豪赞叹。 齐白石从识字到上学-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我两岁。四年(一八六五)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得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香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我的病,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 蓝鲸妈妈和小蓝鲸,遨游在书的海洋,我们是悦读悦享 万名绘本妈妈每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ouwutenga.com/swtxz/6611.html
- 上一篇文章: 看你挺虚的,来碗鸡汤补补肾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